书籍为什么要有章节?
书籍为什么要有章节?

尼古拉斯·达姆斯的研究兴趣包括散文小说;小说的历史;知识社会学、叙事和修辞理论;阅读史;和当代小说。
《从古代到二十一世纪的分段历史》一章,由西奥多·卡汉人文学科教授尼古拉斯·达梅斯( Nicholas Dames)撰写,踏上了跨越两千年的文学之旅,揭示了一种古老的编辑技巧如何成为普遍认可的叙事艺术的组成部分和一种记录时间感觉的方法。
Dames 从古代的文字汇编开始,章节演变为组织信息的工具。他继续讨论福音书最早的划分系统和中世纪浪漫故事的分割,描述了该章节在应用于叙事文本时如何呈现出新的目的,以及叙事分割如何催生了一系列美学技巧。达姆斯讨论了从斯特恩、歌德、托尔斯泰、狄更斯到乔治·艾略特、马查多·德·阿西斯和詹妮弗·伊根等作家。本书涵盖了古代的碑文和卷轴,到当代的小说和电影, 本章提供了读者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熟悉的创作模式的历史。
达姆斯与《哥伦比亚新闻》谈论了这本书,以及文学作品中最令他感动的内容、一本书是否让他与另一个人更亲近,以及他最近在读什么。
你为什么写这本书?
在学术生涯的某个阶段,解决一个长期困扰你的大而未解答的问题是一种自然的冲动。大约二十年前,一位朋友在喝酒时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小说有章节,它们的作用是什么?这是一个“为什么天是蓝色的”之类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可能很深刻。他们以一种很好的方式让你震惊。这个问题指出了一些基本问题,即小说如何训练我们不同类型的时间节奏,以及这些节奏如何缓慢变化,比情节、主题或人物类型的时尚变化更慢。
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它表明我必须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框架中进行思考,这是我在职业生涯中迄今为止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我渴望尝试。这样的项目会让我超出我的直接专业领域,并且需要时间才能加快其他领域的步伐;这意味着我必须稍等一下。终于,经过几年的间隔,我发现自己可以开始这项工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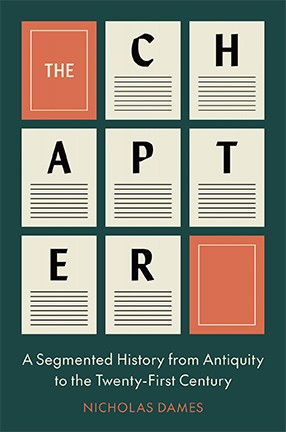
人们必须读你的书才能得到完整的答案,但是你能概括一下为什么书有章节吗?
章节作为分割较长文本的一种模式,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甚至比我们的书籍形式手抄本还要古老。古卷中有章节划分和章节标题,甚至偶尔在以公共牌位形式出版的文本中也有章节划分和章节标题。首先要理解的是:长期以来,章节一直是文学或文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拉丁语中的caput还是希腊语中的kephalaion,这些“章节”的早期化身都源自“head”,意思是“主要元素”或“主要主题”。)
然而,它们最初出现的地方往往是在文本中,我们可以宽松地称之为信息性的古代知识概要,无论是医学、法律、历史还是文学批评之类的东西。章节是一种对长文本进行分段的方法,以实现阅读历史学家所说的“不连续访问”——不是按顺序阅读文本,而是定位文本中可以找到您要查找的信息的位置。要进行这种阅读涉及两个相互交织的任务——将文本划分为有用的单元,并用某种标题标记这些单元,这些标题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找到,有时在单独的列表中。您可以将这两个功能视为分段和索引。一章就兼具了这两点。它是一种促进知识的工具,一种定位装置。虽然它可以由古代作者制作,但更常见的是,它是一种编辑功能,是在文本最初撰写后对其进行的操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技术开始应用于不仅仅是信息性的文本,而且是叙述性的——较长的故事。我最早的例子之一是福音书,从四世纪到十三世纪,它以多种方式分章或划分。 世纪,在不同地方和出于不同目的设计的系统中。(我们圣经中发现的章节可以追溯到 13世纪。)这几种福音叙述的划分系统差异很大:有些有标题,有些没有;有些有标题,有些没有;有些有标题,有些没有;有些有标题,有些没有;有些有标题,有些没有。有些提供许多小章节;其他的,更少,更大。
但正是在这个时候——粗略地说,在古代晚期——章节开始被想象为散文叙事的组成部分,甚至最终成为散文小说的组成部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该分会就会改变其职能——缓慢但果断。它从一种促进信息获取的工具、一种标签工具,变成了一种在叙事中打发时间的技术。它变成了一种时钟,将读者的时间与故事中的时间对齐。
在这一点上——特别是在我们称之为小说的叙事类型中——章节可以成为一种复杂的美学工具,作家可以利用它来塑造读者的节奏;这是一种多维的模式化和同步行为。当然,这与那些标记信息文本的古老标签相去甚远,但有一条可追溯的路线将我们从旧的概念带到新的概念。因此,章节从一个标记装置演变为一个计时装置。
当你写书的时候你会读什么?您在写作时会避免哪种阅读?
有时候,在写作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墨守成规;你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像一张布满灰尘的唱片一样跳动和重复。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喜欢读一些伟大散文家的作品。在你的脑海中暂时保留一些其他的声音是有帮助的,尤其是那些你觉得有亲和力但不完全是你自己的声音,作为一种重置、清理凹槽。对我来说,一些试金石的例子可能是珍妮·迪斯基、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珍妮特·马尔科姆、亚当·菲利普斯。简·莫里斯的旅行写作。才华横溢的年轻散文家和评论家,如弗兰克·关、托比·哈斯莱特、艾米丽·奥格登。这些名字适合初学者。
至于要避免的阅读,很简单——推文。很难不让社交媒体将你束缚在自我意识的束缚中。我的直觉感觉到了。
文学作品中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
诚实但无益的答案——伟大的句子。句子的构造方式绝妙、独特,带有一定的个性印记。例如,亨利·詹姆斯的句子就很有他自己的风格。但是,当然,像每个读者一样,我也有自己特别容易受到影响的特殊场景或主题列表。亲子关系及其涉及的认知类型。时间的不可逆转性,以及我们仍然试图扭转它的方式。还有那些试图与幸福状态作斗争的故事——我经常想,这是最难做好的事情。关于幸福的文献特别少。
一本书是否曾经让你与另一个人走得更近,或者隔阂过你们?
当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给他们朗读无疑是最令人难忘或最重要的方式,一本书拉近了我与他人的距离。相反,我很高兴生活在一个关于书籍的分歧不会以决斗或鸡尾酒会上的拳头结束的时代。但是,(默读)阅读是否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我们和他人之间的障碍呢?作为一个隐士,我很庆幸有这个遥不可及的机会。我第一次读普鲁斯特时,是在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我连续几天呆在室内,拔掉手机插头。这是对我周围世界的神奇拒绝,我希望我能更轻松地重复它。
您最近读过哪些书,您会推荐哪些书,为什么?
JM 库切的《耶稣三部曲》,我姗姗来迟——最后一卷《耶稣之死》于 2019 年出版。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我所知道的本世纪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库切总是冷静超然,有点像个游戏玩家,但这里的游戏与酷相反:它确实将过去的寓言推向了神话,21 世纪的神话。
然后,一整年萦绕在我心头的,是最不超然的一本书——罗马尼亚作家米尔恰·卡塔雷斯库(Mircea Cartarescu)的《螺线管》( Solenoid),我为了写评论而苦苦思索。这是 700 页的死亡金属致幻强度,试图突破每一个可能的界限。包括死亡:卡塔雷斯库在这里的发明之一是一个名为“纠察队”的教派,他们在太平间、墓地、临终关怀中心设立纠察队,徒劳地抗议死亡本身。这对于 21 世纪的情感结构来说怎么样?
你的阅读清单上的下一个是什么?
首先是索菲亚·萨马塔和凯特·赞布雷诺的《语气》,这让我很兴奋,因为它解决了文学理论往往回避的一个松散的概念。我很想读一下杰出的古代晚期历史学家彼得·布朗的新回忆录《心灵之旅》 。我想,我想,对于学术回忆录,对于过去高等教育生活的细节(可怕的、怀旧的、荒谬的),我有一个弱点。
你正在举办晚宴。您会邀请哪三位学者/作家,无论是已故的还是在世的,为什么?
我会信任朋友和家人进行亲密、富有同情心的聚会。为了这个机会,我宁愿把晚宴当成警句家和独白家、剪辑大师和猫腻大师的剧场,让他们决斗,看看谁能在法庭上表现得最令人难忘。如果这是我的幻想,我会坚持小说家,那些喜欢谈话才华的人,甚至——或者特别是——当它是好斗的时候。
让我们从司汤达开始,他是拿破仑时期的士兵和后帝国时期的外交官,后来成为客厅竞争的记录者,他讨厌无聊或乏味。将他与同时代的简·奥斯汀放在一起,简·奥斯汀与他除了对机智的社会侵略性的深刻理解之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然后我会请穆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来,他的笑话可能会让人流血。这很可能会成为一场灾难。我会牢记每一个字。
 哥伦比亚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留学方案申请